味蕾生意
葉秀燕|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
我問做生意的朋友,在台灣什麼錢好賺。朋友說:「不怕辛苦,做吃的一定會賺」。也難怪,在台灣每個觀光景點,除了名產紀念品外,一定有餐廳、飯館、美食小鋪,還有蚵仔煎、葱油餅、臭豆腐,烤香腸和大腸包小腸。
在高高的山頂上,賞白雪喝滾燙冒煙的熱熱貢丸湯,一點都不稀奇。自稱熱愛「自然」的爬山健行客,把山徑圍起來,公地成私地,煮水泡茶,野炊兼唱卡拉OK,硬把野地自然給家居化,廚房用品應有俱全,「大家逗陣來泡茶」,如此佔地為王,破壞自然景觀,大概是台灣特有的登山飲食文化。
坐公共交通工具,火車上最常看到的仍是食物。零食、麵包、飲料、飯糰、便當,還有名產,太陽餅、鳳梨酥、花蓮薯與雷古多,還是和吃吃喝喝有關。
在大陸旅行時,總看到有人抱著大西瓜趕火車。車廂裡到處是飄著「康師傅」的各式泡麵香,隨時有人在吃,為自己加熱水,續沖一葉葉飄在玻璃瓶的茶水。茶水間熱水沒了,旅客抱怨、生氣,甚至爭執吵架,都因為空水桶。中國的朋友說:「民以食為天」,「要吃吃喝喝,才像出遠門嘛!」海峽另一邊說:「呷飯皇帝大。」不論民主與共產,兩地政治迥異,對吃的重視,不分上下。「吃飽沒?」是漢語民族共同的招呼語。
台灣的小籠包進駐上海,價格是台灣的兩、三倍。上海人擠破頭、排長龍,還是要嚐嚐台灣來的小籠包。前幾年,台灣人搶購葡式蛋塔的盛況,絕不輸小籠包。報紙上說,有人為了一盒蛋��塔大打出手,加了火氣和鮮血的蛋塔,會不會更可口?

吃進「自然」。葉秀燕提供。
現在想吃萬巒豬腳,不一定要開車到屏東。東海的雞爪凍,郵購宅配也能到家。這的確是個流動的時代,也是個不動的時代。網路購物,讓人不必出門,就能滿足口腹之慾。這是科技的神奇。
台灣公路省道旁,一間間便利商店,比鄰對門而開。主要道路500公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的現象,更讓人覺得嘖嘖稱奇,佩服台灣的「便利性」。在不同的便利商店,賣得最好的還是食物和飲料。曾經一顆小小的茶葉蛋,讓一家面臨經濟危機的便利商店,起死回生。我們的便利飲食文化,連始作俑的日本人也望塵莫及吧?
現在過年,更可以在便利商店預訂年夜飯,宅配到家,讓不想大費周章,或沒有時間下廚的人,也能輕鬆過個「便利年」。每回看到這樣的「年味」海報,總要想起阿嬤上代的生活方式和媽媽純手工製造的年菜佳餚。不禁要問,這樣「便利」的年,如何記憶?節慶與食物如何串連?
我不吃麥當勞和漢堡王,也不喝星巴克咖啡。飲食要多元,經濟卻不能獨斷。這是我反全球資本主義的日常生活飲食實踐。然而,速食文化,卻有我很多學生的成長記憶。他們在麥當勞做功課,閒扯淡,聊天說地,消磨他們青澀的歲月。大學生到星巴克等人約會,談情說愛。人類學者吳燕和指出,漢堡、咖啡不是舶來品、外來文化,這些源自西方的食物,已成了當代台灣年青人日常生活的飲食文化之一。
在台灣各地的風景名勝及旅遊景點,結合當地農產品與族群特色的餐點與名產,更成為近年業者競爭的商機賣點與招攬遊客的策略。原住民「風味餐」的興起,和文化與生態觀光旅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原住民風味餐廳的看板符號。葉秀燕提供。
從原住民餐廳業者的訪談資料及田野觀察結果顯示,業者對「風味餐」的飲食文化生產概念,有的根植於日常生活的經驗;有的來自和特定過往童年記憶的連結;有的「看媽媽怎麼做」學習而來;也有「學習自烹飪班,自己再創造」。有「傳統」、有「創新」,更有「創新的傳統」,不同脈絡的文化混融,各自發展出其獨特的「原住民風味餐」。如果說,在「邊緣」的文化環境中,擁有權力便擁�有「發言權」,我們也可以說,誰擁有原住民風味餐廳,誰便擁有賦予「風味餐」意義的權力、以及對餐廳賦予新的意義與支配性。業者做為原住民文化的能動者(agents),誰是老板,誰便擁有定義、生產、翻釋、詮釋、協商、形塑、操弄、展演、解構、再生產「風味餐」的權力。筆者認為,飲食創意沒有標準,風味不是唯一。
原住民風味餐廳彈性「配菜」,山蘇、龍葵、劍筍、馬告、飛魚、蝸牛、檳榔花、竹筒飯、野菜小魚湯、香蕉糯米飯、石板烤山豬肉,不僅可以配合不同口味、人數的需求,更可依照付費價格的高低,搭配不同的原漢風味套餐。親切好客的業者,也不時走出廚房,解說原住民文化知識,讓消費者/觀光客興高釆烈學習如何敲開「竹筒飯」、如何「吃香蕉糯米飯」、如何分辨「野菜」。原住民風味餐賣的是「異」文化的體驗與地方經驗的收集。
原住民風味餐翻轉「原漢」二元對立的族群張力,彙集了各種尚未接合的社會現實—原漢族群彼此尊重、地理混合羼雜、文化相互交融、空間越界、不分你我,餐桌上想像「族群融合」,吃進原味,想像「你濃我濃」,在「風味餐」裡實踐「原漢文化交融」。
原住民風味餐/廳不僅可以賣「原味」賺錢,也讓台灣的飲食版圖,建構出多元的族群文化空間與餐飲形式。「味蕾生意」也可以做為「社會運動」,讓「黃昏民族」擁有傳承及發揚其異於主流漢文化的「差異政冶」(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s)的可能性。
筆者認為,原住民風味餐廳的興起與流行,和現代社會中對「異��文化」的商品化、表演化及消費化有著密切關係。原住民風味餐廳在台灣,可視為當代流行的「異族情調」,對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,原住民日常生活的飲食物質文化,是陌生的經驗,如果原住民風味餐可以做為原住民「傳統生態知識」再生產和文化展演的「文本」,原住民風味餐廳,用「自然」和「健康」所帶動的飲食文化,正是資本主義與觀光遊憩發展的共謀、與消費文化生產的模式。資本主義對文化生產與複製的穿透力,也正是近年「原住民風味餐廳」可以獲利市場的主因。誠如文化評論人馮久玲指出,二十一世紀文化商品絕對是好生意。文化買賣,味蕾生意,不僅是少數族群的生機,更是好商機。
對食物的思索與飲食文化的研究,可以開展我們理解與體驗族群文化展演的多元流動與不變的固著性。原住民風味餐用味蕾來豐富飲食文化經驗,建構台灣飲食版圖的文化位置與地景,不僅擴大原住民經營者的文化詮釋與發言權,同時提昇多元文化交流的平臺。然而不可否認,卻也形塑了風味餐及原住民文化被符號化消費的社會事實。
台灣社會不斷在變化,從飲食文化、味蕾生意,就可看出端倪。你嚐出不同在地和全球的味道嗎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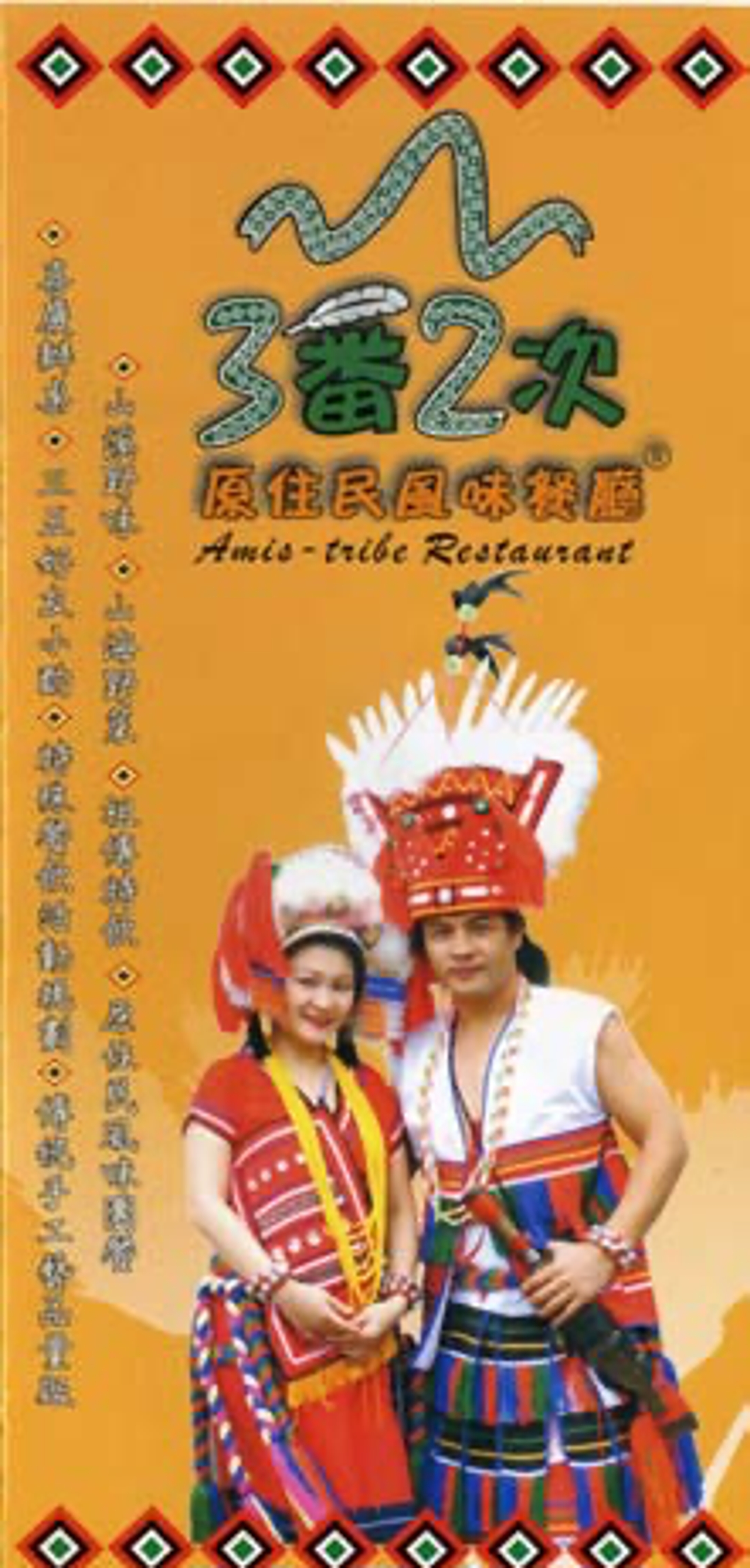
三番兩次-大家來做「番」生意。葉秀燕提供。
歷期視界